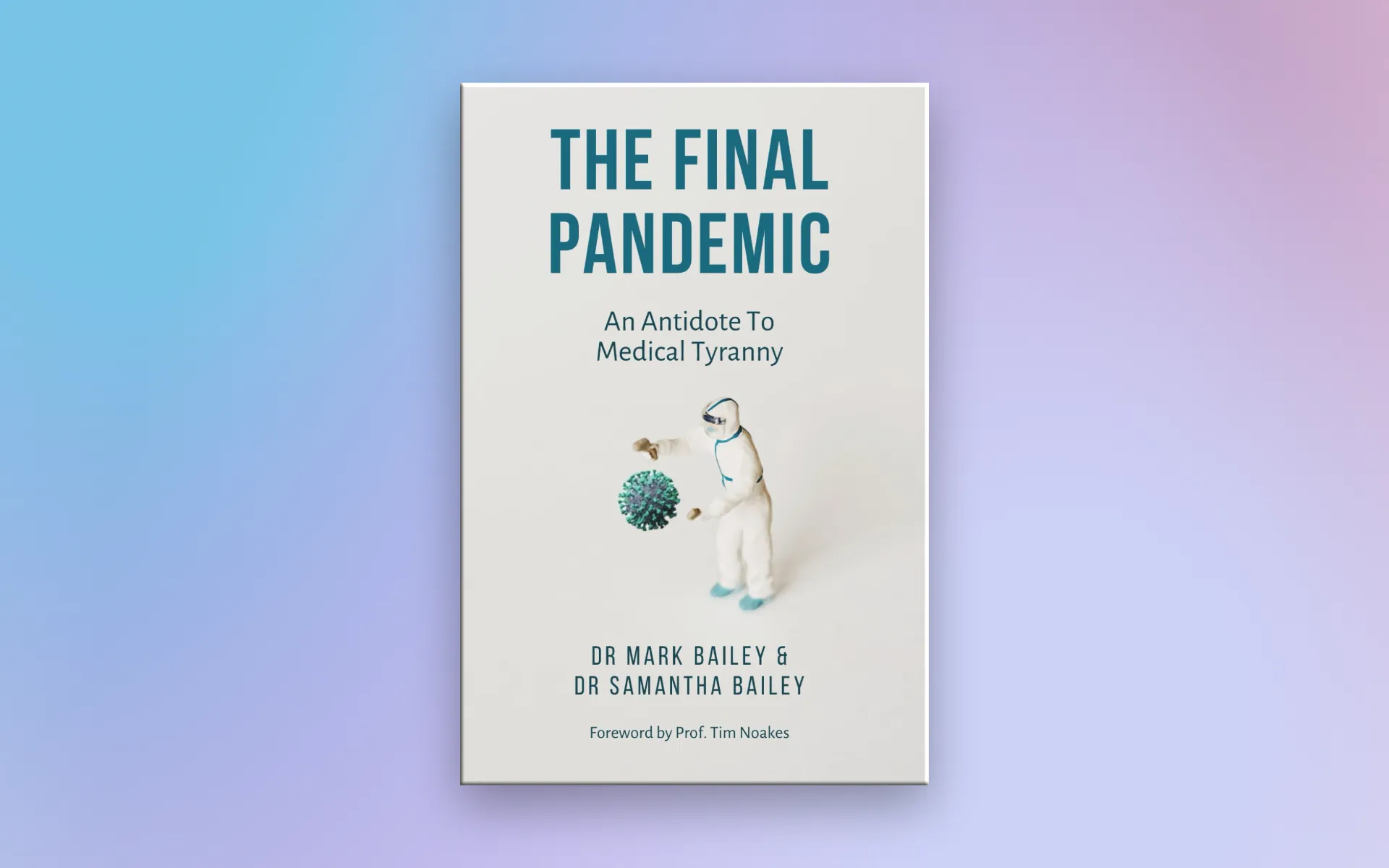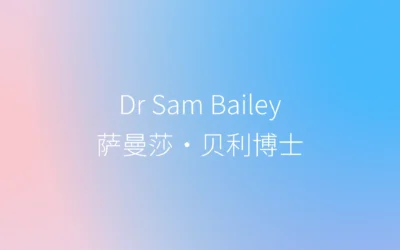或许历史上最著名的“超级传播者”故事当属玛丽·马伦(Mary Mallon,1869-1938),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伤寒玛丽”(Typhoid Mary)。历史记载称,这位爱尔兰裔美国厨师在 20 世纪初的纽约市地区辗转于不同家庭之间,据信“感染”了 51 到 122 人。维基百科中写道,她是“美国第一个被确认的无症状携带伤寒沙门氏菌(Salmonella typhi)的人”。这里充分展示了病原理论的矛盾之处,其支持者对“病原体”的存在和病人发病与否之间缺乏关联这一事实毫无异议。1907 年,卫生工程师乔治·索珀(George Soper)帮助逮捕了玛丽·马伦,并于 1939 年在《纽约医学院公报》中描述了她的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玛丽·马伦是在 32 年前,即 1907 年。那时她大约 40 岁,正值体力和智力的巅峰。她身高五英尺六英寸(1.68 米),金发碧眼,肤色健康,嘴唇和下巴带有一丝坚毅。玛丽身材不错,若非稍显丰腴,甚至可以称作健美……事实上,我不需要检验标本来证明玛丽是伤寒病菌的传播源。我的流行病学证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费力地查清了每一起暴发,确信全都是由玛丽引起的。”
然而,索珀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伤寒“病原体”,特别是伤寒沙门氏菌能够导致伤寒热。在历史上也没有其他人提供过类似证据。2014 年,《临床传染病》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声称,通过让志愿者吞下这种细菌,使一些人患上了伤寒,但该研究存在几个重大的科学缺陷:
- 伤寒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疾病,描述如下:“高热逐渐发展,伴随精神错乱。躯干部位出现皮疹。细菌繁殖的部位可能会发炎、溃烂,导致肠道出血或腹膜炎。患者极度虚弱和消瘦;如果不治疗,死亡率可达 25%。”然而,在 2014 年的研究中,报道称 40 位吞下细菌的志愿者中:“挑战过程耐受良好;没有参与者需要住院、静脉注射抗生素或输液。”这与典型的伤寒表现并不相符。
- 大多数参与者并未出现任何发热现象。为了将“感染率”提高到 50% 以上,研究人员不得不降低标准,采用“替代诊断标准”。
- 在自然条件下,人们通常不会摄入如此大量且浓缩的细菌,研究中的细菌剂量远高于常规暴露情况。(参见“剂量决定毒性”1 的相关说明。)
- 该研究中没有设置对照组。本应设置一个同等的志愿者对照组,给予去除细菌的同样的培养基液,或给出“非致病性”细菌,以观察他们会出现何种症状和体征。
- 研究并未进行双盲设计,因此志愿者和研究人员都知道被吞下的细菌被认为具有潜在的致命性和“全球重大健康问题”的风险。(这被称为“反安慰剂效应”:在反安慰剂效应中,若实验对象相信可能存在副作用,他们往往会体验到这些症状。)
仅凭第 1-3 点就足以对沙门氏菌是伤寒病因的假设提出严重质疑。第 4 和第 5 点则完全使该研究无法符合科学方法,因此从设计上看,该研究根本无法用来测试任何假设。换句话说,他们的主张完全站不住脚,也从未有确凿证据表明细菌是罪魁祸首。不幸的是,自乔治·索珀以来,似乎不再需要找到这些缺失的证据——人们只是理所当然地认为病菌“事实”早已在实验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当然,这仍然留下一个问题:为什么玛丽·马伦工作的家庭中常常会出现伤寒病例?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无法得到解答,因为我们只有索珀的少量评述,几乎没有可验证的科学数据。完全有可能的是,作为这些家庭的厨师,她的卫生习惯不佳,以其他方式污染了食物。食物中毒并不等于“感染”,同一地点的病例聚集也不是“传染”的结果,而是大家从同一来源摄入了相同的毒素。
此外,也很难排除这个广为传播的故事背后可能有更复杂的动机。该事件被称为病原理论的经典事例之一,但缺乏可验证的资料让人怀疑其是否被夸大或扭曲过。甚至乔治·索珀在《纽约医学学会通报》中发表的相关记述,也是在所谓事件发生三十年后才发表的,而这一记述构成了“超级传播者”概念的基础。
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是,“病毒谎言学”(ViroLIEgy)的迈克·斯通(Mike Stone)深入研究了 19 世纪后期病原理论的发展。他指出,为了维持病原体模型的完整性,逻辑和科学方法被便捷地忽视了,“无症状携带者”的概念被引入:
“当科赫(Koch)提出著名的科赫法则(用于证明任何微生物导致疾病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时,他的逻辑和常识告诉他,一个‘致病因子’不应出现在健康人身上。然而,对于科赫来说……他经常在没有疾病的个体中发现这些‘致病’微生物(尤其是结核、霍乱和伤寒的细菌)。因此,他无法满足他的第一个法则(即微生物应大量存在于所有患病个体中,而不应存在于健康个体中),以宣称他所发现的微生物是疾病的真正原因。不愿放弃名誉、财富和声望的科赫扭曲了自己的逻辑,引入了无法证伪的‘无症状携带者’概念,以维持其发现的完整性。”
- 来自拉丁语,“dosis sola facit venenum”,意即“剂量决定毒性”。即使摄入大量水也可能导致严重症状甚至死亡。 ↩︎